Physical Address
304 North Cardinal St.
Dorchester Center, MA 02124
Physical Address
304 North Cardinal St.
Dorchester Center, MA 02124
很多人认为,对咖啡爱好者而言,速溶咖啡是下下之选。不过,在忙碌的时候,速溶咖啡的便捷性,却是无可取代的。 我先承认,已有多年未喝速溶咖啡,只在踏入咖啡世界之前,倒也喝过三、四年。 我不会贬低速溶咖啡,它的方便性,特别对于“咖啡因需求者”而言,的确不是任何其它咖啡可比的。比如我有一位朋友,某次连夜赶写论文,连冲咖啡的时间都匀不出来,他采取非常极端的作法:两大匙速溶咖啡粉直接倒进嘴巴,然后喝一大口热水,将粉和水冲进胃里。多年来他一直强调,他那篇论文是以这种方式支撑出来的。 当然,站在咖啡爱好者的角度,速溶咖啡欠缺咖啡真正的美妙,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大型咖啡公司,像雀巢、麦斯威尔等,投入大笔硏究经费 […]
春到来时,程依香隔壁那间小屋,卖掉了。整天进进出出的工人和施工声,吵得她不得安宁。终于,她去了船吧。 “天啊!稀客!”老巴问:“多少年没喝咖啡了?” “二年多了。”小香说。 “我还没见过有人真能把咖啡戒掉的,妳是我遇过戒喝最久的一个!” “我没有戒,只是刚好没有想喝。” 老巴摇摇头,煮着咖啡,香气再度进入程依香的心肺。她一闻就知道没救了!那味道就像老朋友。不是香不香的问题,而是一种感动,像自己身上失去多年的一部分,她趴在桌上一动也不动,“哦……天啊!真是要命的味道!” “呵呵,想念吧。”老巴闻着搅伴器,“妳知道吗,咖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秘密情人。” “秘密情人?” “看不见,但真实感动在心里 […]
我在前往伊斯坦布尔前,辗转拿到了君子们咖啡馆的地址,在老城区,苏里曼尼清真寺不远处。土耳其文的地址,由于不理解单词的意思,显得非常不真实。 它吸引着我一定要去寻着,因为这个咖啡馆据说建于16世纪旧咖啡馆的原址。当时,咖啡作为来自非洲的喷香饮品刚刚进入奥斯曼时代的伊斯坦布尔,并在伊斯兰世界里流行开来,成为帝国饮品,这座城也还叫君士坦丁堡。从游客手里看到过一张关于这家咖啡馆的照片,照片里的咖啡客,未见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倒是大都沉静地埋头抽着水烟,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轻绕,乳白色的。他们面前的小矮桌上,放着描金小杯盏,小盘子里横着一柄银色小勺子,这仍旧非常奥斯曼,与维也纳皇宫城墙外的中央咖啡 […]
我不是咖啡瘾者,一天只要一杯咖啡垫底,顺喉顺意,身心荡漾,醒脑也!就算一杯Triple Shot磨豆,也没必要戒咖。叹咖啡快乐时光,总懒得批评罗布斯塔咖啡种邂逅化学奶精后,又去幽会高温蔗糖那回事。这根本就是慢性自残的三合一,就甭提三合一咖啡啦!只是蛮奇怪,人在国外旅行时,一旦惊闻阿拉比卡咖啡香,就有股按耐不住冲动。再来一杯卡布奇诺,赞!当然,周边好像不仅仅是我一人是那么的无聊吧?但,说叹咖啡是无聊事,注定是要得罪咖啡不归客!瞧瞧你家附近,肯定有一家咖啡馆在埋伏着。天天呼唤,“你咖啡了吗”? 其实,亚洲的一杯咖啡,从哪天开始,无端端染上了欧洲人的习惯;越过历史,攀登文化,成了时下年轻时尚,品质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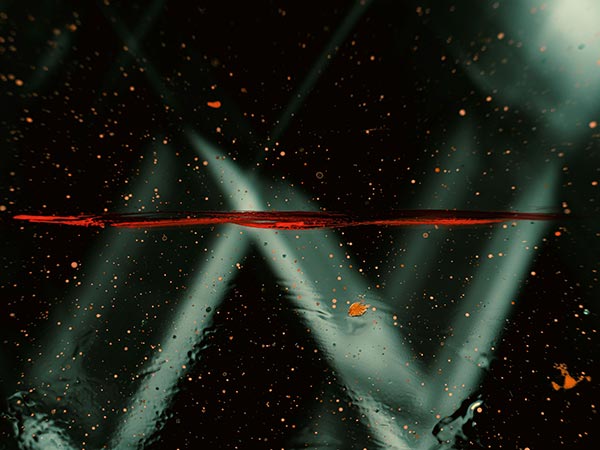
程依香躺在病床上睡得很沉,床边也睡了一个人──胡天岚。 钟少蔓摇醒胡天岚,“小岚,妳回去休息吧。” “妳来了,动作真快。”钟少蔓一接到胡天岚的电话,便由北都赶下来。这时已是午夜,胡天岚柔柔眼醒来,“她打了助眠药,医生说她需要睡眠。” “嗯,我知道,她醒了我会通知妳,回去顾照小孩吧。” 隔天,程依香出院,胡天岚开车来接她和钟少蔓。回到音乐小屋,程依香脸色依然惨白,她坐在大红蛋椅上,坐着坐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海依然在那,但她已经不一样了。 小岚偷偷问少蔓:“不能喝咖啡,有那么严重吗?” 少蔓说:“妳忘了咖啡把她改变了多少吗?” “说的也是。” 少蔓说,“小香,公司那边我帮妳请了假,妳先休息一阵子。” […]
除非老板不在乎获利,否则冰咖啡通常都比热咖啡贵,特别是考虑到时间和空间成本,实际上贵多少不一定。 卖冰咖啡可以让咖啡店赚一点钱,但冰咖啡花费的时间和工夫限制了获利,成本也比较高。 冰咖啡需要冰和制冰机,冰咖啡通常用塑胶杯装,价格比纸杯贵,客人通常用吸管喝冰咖啡。纽约Think Coffee老板谢尔说,杯子和吸管等东西加起来,冰咖啡的成本多出约20%。 另一家咖啡店的老板表示,冰咖啡的成本,因店家服务的方式而异,比较漂亮的杯子和纸巾成本也更高,不过多数老板在设定饮料价格时就考虑到这些成本了。 气候也有关系,宜人的春天对咖啡店大有帮助。Joe Coffee老板鲁宾斯坦说,在一个温暖的春天,生意会比 […]
咖啡是舶来品,最初传入中国时,必是先出现在了新派人物聚集的上海。 最早提供咖啡的,是英国药剂师J. Lewellyn在1853年于花园弄(今南京东路)1 号开的老德记药店。它虽叫药店,但也经营糕点和洋食。 这口感酸苦的奇妙棕色液体一开始被称为“咳嗽药水”,随着西餐的推广和普及,到后来竟成了时髦之物。 1909年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词》中,就已有描写咖啡的诗句: “考非何物共呼名,市上相传豆制成。 色类沙糖甜带苦,西人每食代茶烹。” 同年,上海基督教会的美国传教士高丕第夫人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西餐烹饪书《造洋饭书》,其中也提到了咖啡,并说明洋人饭后饮咖啡助消化。到了1946年时,上海已经开了近两百家咖 […]
台风走了,风雨仍一阵大一阵小,程依香丢了件轻便雨衣给柴井康。 “妳疯了吗?”柴井康问:“我们要用走的?” “用走的可以到,但我们还是开一段车好了。” 他们开到大草原的尽头,转入一条小径,路愈来愈小,出现一个小洞穴。洞穴口,有盏微弱的小灯。 程依香说:“灯亮着,很好。”她指着空地,“停那台车旁边。”空地上已经停了二台车。 “不会吧?这里真的有咖啡馆?”柴井康真的很怀疑,四周全是荒山野草。 他们下车,冲向小洞穴。在洞穴里脱掉雨衣后,程依香说:“拿出手机。” “干麻?” “手电筒。” “什么?” 程依香突然正经地看着柴井康说:“接下来这一段路很黑、很暗,深不见底。你信得过我吗?” 柴井康笑着说:“应 […]
很多年前(编者注:1980年代中期),我失业在家,对自己的前程正感到困惑难明,几位朋友打气说:“开家咖啡店吧。”因而我在台北东区还不热闹的街道里有了一家很小的咖啡店。很快地,因着我原有的工作背景,咖啡店主要的来客是新闻记者、作家、文艺圈与影剧圈的工作者,还有,和这些人过从甚密的“革命者”。 革命者,和其他族群一样,也是多样多面,他们有的热情洋溢、有的鬼鬼祟祟;有的博学多闻,有的猥琐草莽;有的大声喧哗,有的静默警戒。但他们共通对社会的不满溢于言表,永远有你不知道或不敢相信的内幕消息;更有趣的,革命者共同的特性之一,是不爱付他们的咖啡钱。 革命者和僧侣一样,他们是习惯受供养的人;僧侣漠视此世,推销 […]
一大早程依香的牛铃又响了,她打着哈欠开门…… “妳为什么不开手机?”柴井康在拉牛铃时,发现门口有块小木牌上刻着:音乐小屋。 “有人睡觉时开手机吗?”程依香一脸睡意地靠在门边。 “有啊。”柴井康精神地说。 程依香不耐烦地说:“我今天没力气带你去咖啡馆,改天再说吧。”程依香精神的确不好,她感觉头有点晕。 但柴井康不放过她,“你不知道台风要来了吗?” “有吗?” “快十二月了还有台风,不是很奇怪吗?” “那你还来?” “我是来扫庭院的,上次去船吧那次我还没付呢。”柴井康笑了。 “哦,那个没关系啦。”程依香打了个哈欠。 “有关系。我不喜欢欠债的感觉。” “随便你。工具在车库里,记得扫干净一点啊。”程依 […]